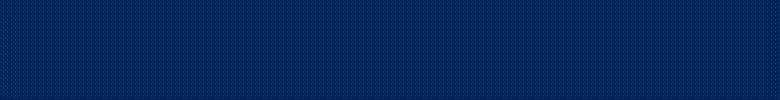王強 :潮起湄南:在文明交響中書寫民間社團的橋樑之歌 ——記泰國泉州晉江聯合總會與世界泉州青年(泰國)聯誼會
稿件来源:菲律賓商報
2025年06月18日 00:31
當晨光灑落在曼谷大皇宮的金頂,湄南河畔水氣氤氳,輕撫鄭王廟飛簷;遙遠的泉州九日山晨鐘悠悠傳來,似有千年回音,喚醒一段跨越時空的“下南洋”記憶。從刺桐古港到暹羅灣畔,從冰裂紋青瓷上殘存的工匠掌印,到沉睡於海底的壓艙石,這條千年航路早已超越貿易之途,而成為語言的通道、記憶的水脈、認同的河流,蘊育出異地紮根、生生不息的華人文化社群。
在這條文明長河中,民間社團猶如湄南河上駛動的長尾船,以歷史為槳,情感為帆,書寫出一道道連結族群與文化的航線。他們既是漂泊者的精神港口,亦是語言與信仰的守望者,更是構築文明橋樑的靈魂擺渡人。
一、始於唐風宋韻的帆影
自唐宋以降,泉州港商舶雲集,素有“東方第一大港”之譽,成為中外文明交會之所。彼時阿瑜陀耶王國已接納自泉州與潮汕遷來的商旅;素可泰遺址間的青瓷殘片,彷彿仍訴說著閩窯工藝的溫度與記憶。泉州灣的季風與暹羅灣的潮汐共振出海上絲綢之路的節奏;市舶司的帳冊、三寶公廟的香火,皆靜靜記錄中泰文化的交融與互鑒。
在這條海路上的華人,不僅是文化的傳播者,更是文明的學習者與調和者。他們攜來的不僅是貨品與技藝,更帶來語言、信仰與生活的精神紋理,使“禮儀之邦”的風骨,在熱帶雨林與佛塔之間綿延展開。
二、明清海禁下的奔流
即便於明代海禁嚴峻之時,泉州人“向海而生”的文化本能從未熄滅。十七世紀,隨季風南行的閩南移民陸續定居暹羅,築起異鄉為鄉的命運共同體。吞武裡王朝的鄭信,以潮人之身扭轉乾坤,重塑政局;至拉瑪一世時期,華人在稅務與治理體系中已居中樞,深度參與社會重建。
他們不僅是經濟參與者,更在制度設計、信仰重構與語言延續中,實現了一種兼容並蓄的文化秩序。文化的韌性,恰在歷史逆流中愈見其深。
三、社群共生與文化韌性
民間信仰從不孤立生成,而是在多元互動中漸次交織與融合。泰國寺廟中,清水祖師與本土神祇並祀共壇;媽祖與象頭神共享香火空間。北大年府的慈靈宮、曼谷的七聖媽廟等,皆為信仰協商的實踐場域,展現“三教合一”的信仰圖景,體現閩南文化所蘊含的跨文化包容智慧。
“善堂文化”則進一步彰顯儒、釋、泰三道合流的倫理實踐,其核心蘊含儒家的仁義、佛教的慈悲與泰族“sati”(正念)之精神,構築起連結世代與族群的慈善網絡,成為泰華社會中維繫精神的溫潤河流。
語言與族群記憶,如涓涓細流,滋養著南洋大地的文化肌理。童謠〈天烏烏,欲落雨〉至今仍在漁村低迴吟唱;泰語中的“頭家”、“阿兄”、“龜”等閩語音譯詞,則是語言滲透的文化年輪,靜靜印刻著融合的歲月痕跡。
更深層的文化根系,則潛藏於僑批中斑駁的墨跡、私塾裡琅琅的書聲、會館中高懸的對聯。語言在流轉中傳承,記憶在傳承中凝聚,而認同,則在這條無聲卻堅韌的文化水系中,悄然生根,薪火相續。
四、合作共贏:經貿與文化的雙重脈動
從“走街串巷”到“出海登陸”,經貿與文化早已並行不悖。拉廊許氏家族的鑽石切割技藝——“雙玫瑰切割法”專利,已成為曼谷珠寶展上的閃亮名片;晉江企業家的航運網絡,覆蓋東南亞八成石材運輸,將南安水頭與泰國建材市場無縫銜接。
根據泰國中華總商會2024年報告,潮汕與閩南後裔掌控65%的橡膠貿易與52%的農產品加工,經濟網絡已成為文明互動的重要主軸。文化亦在創新中不斷延展:即將於2025年在湄南河畔舉辦的“閩南文化節”,將清水祖師與媽祖神像迎入曼谷藝術文化中心;舞獅與泰拳同台共舞,沙茶麵與肉骨茶共飄芳香,構成一幅信仰、藝術與生活交織的當代表現圖景。
五、水的隱喻與未來的航向
在泰語中,“水”象徵潔淨與滋養,亦寓意流動與再生。而閩南語的“水客”,從昔日海上商旅之稱,演變為今日文化流動與族群穿越的隱喻,象徵著記憶的流轉、認同的生成與歷史智慧的延續。
早在1292年,蘭甘亨石碑便刻下:“水為民生之本”,其治國理念與當代所倡“綠色發展”與“命運共同體”不謀而合。水,不僅是自然資源,更是治理的語彙、情感的介質與文明的語言。
對農耕社會而言,水是命脈;對遷徙族群而言,水是鄉愁的流動體,是記憶的寄存器。從清水祖師的慈悲精神,到媽祖橫渡天海的守護形象,水已超越其物質性,成為連結過去與未來的隱喻性橋樑,象徵著人類文明的不息長流。
尾聲:潮聲不息,橋樑永續
湄南河奔流不息,泉州港浪花依舊。民間社團如舟,以語言為帆,以記憶為舵,在時代激流中堅定前行。他們既記錄族群歷史,也參與書寫人類文明的長篇史詩。
當文化節的燈火再度點亮曼谷夜空,當華社青年在傳統與創新之間尋找身份的座標,中泰民間交流的潮聲,將如湄南河水,綿延不息,通往更廣闊的文明彼岸。
潮湧湄南,未來可期。